工地挖出无名女尸人死了3年手机却是半年前的新款!
肮脏的百叶窗把阳光撕得支离破碎,照片上的那堆白骨显得愈发斑驳,白骨的旁边放着一只手机。
他抽动了一下嘴唇:“我托学法医的朋友私下看过,这个人至少死了三年,但身边的手机却是半年前才上市销售的。”

看他现在西装笔挺的样子,应该是混得不错。据说工作才满两年就成为某大型房地产公司的中层干部,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。
“我只是有点好奇。”我一边凑近他,一边深深地凝视着他,“高中毕业后你我就没了联系,可你现在的态度却像咱们昨晚才共进晚餐一样。是谁给了你这样的自信?”说着,我把视线投向那张照片:“给我看这张莫名其妙的照片,是你学的泡妞新招?”
他尴尬地笑笑,开始转移话题:“这张照片是我在一座即将拆迁的旧楼里拍摄的,尸骨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。说到这里,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波动,嗓音也跟着变调,“准确地说,是天花板开裂了,它从夹层里掉了下来,恰好砸到我的头上,差点把我砸晕。”
“那你该去医院检查一下,而不是跑到我这里来。”我凉凉的说道,“我是私人侦探,又不是医生。而且我不管这些刑事案件,你要做的是去找警察叔叔,懂吗?”
“我没有报警,那地方是我们公司的重点项目,施工队伍早已准备就绪,就等一声令下了。我磨破了嘴皮,总算让房主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,要是为了这种事耽误了进度,无法按期交付,公司会损失惨重。”他继续自说自话。
“好个忠心耿耿的员工,可惜我不是你的老板。”我不冷不热地说,“事情很离奇,但跟我丝毫没有关系。你还是回去吧,记得替我向你父母问好。不送了。”
安言像是没有听见我的冷言冷语,接着说道:“还记得小时候咱们巷子东口的灰色小楼吧,就是一层的门窗全部被封住,只有二楼有人住的那栋。你还记得吗,一楼的走廊里的日光灯永远都是忽明忽暗的,咱们还去探过险。”
“这么想的人是你。既无根据也没逻辑,却能把自己搞得坐立不安,这种感情大概就是喜欢吧。”我站起身拍拍他的肩膀,“别不好意思,咱们小时候一起胡闹时,我就知道你喜欢她,只是没料到会持续到现在。”
“喜欢一个人并不是什么耻辱。毕竟我们三个的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。”我笑了笑,随即沉下脸,“你兜那么大的圈子来找我,干嘛?还怕我对你余情未了?”
他想解释,被我阻止,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正在播放的电视新闻上:某个知名男作家心脏病发身亡,而一周前他还在书店里签名售书。对他的离去,粉丝悲痛万分。
“人生无常。”我轻喟一声,“前些日子我还特别研究了他的作品......你有多久没见过薛雀了?”
“啧,记得这么清楚,也真不吉利。”我从衣架上取下大衣,“好了,咱们去重温童年时光吧。”
我在梦中经常回到老宅,但三年以来始终没付诸实施,尽管它距离我现在的住处仅有5公里。
秋日温暖的夕阳斜斜地照在陈旧的红砖上,加上空气中飘扬的尘土,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柔和的光晕。虽然这里早已无人居住,但我似乎看到了昔日的邻居从窗里探出头,用微笑欢迎一起从学校回来的安言和我。
“没什么。”我摇摇头。安言打断了我短暂的出神,钻出车门的瞬间,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我自己,利落的短发,轮廓瘦削,眼神凌厉,神情冷漠,加上一身黑色大衣,足可以拒人以千里之外。
如果往日的邻居们看到了我如今成了这幅模样,不知是否能和当年倔强骄娇憨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。
我们走到了那栋灰楼的面前,它是这条小巷里唯一一栋水泥结构的楼房,建筑风格也迥然不同。听说这里是日伪时期某个官员的住宅,他为了彰显身份,特意设计出了这种僵硬死板的外观。
自以为是的门外汉最擅长的能力就是把事情搞砸,这地方使用了不到十年,楼下便严重透寒,只好封闭弃用。解放后这里变成了普通民居,二楼的住户每天回家都要经过那条冗长漆黑的走廊,以至于他们宁可牺牲共用面积,凑钱在楼上修了个公共厕所,也不愿意去使用一楼阴暗潮湿的那个。
那条走廊出现在我的面前,与昔日的残像截然不同:日光灯熄灭了,旁边有一道光柱直直地投落到地面上,碎裂的木板与砖头瓦片散得到处都是。我走到那里向上望去,发现这地方已经被砸穿,光线来自二楼走廊的窗口。
“为了确定夹层里再没有别的古怪东西,我和房主一起砸穿了这里。”安言解释道,“你知道的,那个夹层其实是壁炉的烟道,直通后边的烟囱。”
“木板早就烂透了。”他捡起块木屑递给我,触感粘稠湿冷,像是一块被吐出的口香糖。
“它和死人在一起,直接揣在怀里总觉得有些不舒服。”他说,“你尽可以拿出来看。”
“哇哦,旗舰款。”我叹息道,“早就想买一部了,总是不舍得,用它殉葬真是浪费......走吧。”
到了底层,我找到一家专卖手机的店铺,径直走进柜台,推开货柜旁边的门,里边是一个宽敞的工作间。拉开门后,一个胖子抬起头,看到我,脸上露出笑容。
他的眉毛上好奇地堆起两块肉,但没有多问:“需要花点时间,您先坐着等一会。”
十几分钟后,胖子回来了,扬了扬手里的单子:“这部手机是四个月前卖出去的,就在这个卖场。”
“吴宗颖。”我拿过单子读出声,“这字真够难看,名字也应该是假的,电话很可能......”
“手机还给你。”胖子虽然不明就里,但见到气氛有些尴尬,便岔开话题,“受潮黑屏,但没大问题,我刚才顺手吹干了一下,可以正常显示了。”
“谢谢。”我心不在焉地点点头,忽然意识到了什么,“......这手机是开着的?”
“是啊,刚才我看了下系统信息,已经连续开机三个多月了,看来机主没有关机的习惯。现在电量还剩一大半,之前只是受潮黑屏了,机器没大问题。”
一个三年前死亡的人,却用着新款手机。死人还能按时给手机充电?这太匪夷所思了。
离开地下商场,我和安言坐在绿化带旁边的凳子上,相顾无语,直至夜色降临。我没有问他任意的毛病,这似乎反倒令他坐立不安,主动提出了这个建议: “要不要去看看尸骨?”
“我对尸体解剖没研究,既然你能找到稳妥的地方收藏它,那么鉴定结果应该是准确的。”我转悠着手机,“机主没有在里边留下任何痕迹。通话记录和短信全是空白的,手机卡也没有插,大概与幽冥黄泉通话是不需要拨号的。”
“我们无法解释电池的问题,但我相信买手机的肯定是活人。”我把手机交还给安言,“起码商家收到的钞票事后没有变成冥币。”
“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很多。”他黯然道,“我刚才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,毫无头绪。”
“但是既知道你的手机号码,又知道老房子烟道的人就不多了。”我淡淡地说,“我算是其中之一,不过很显然,我还活着。那么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另一个人了。”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,或者说就没有答案。我和她是朋友,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为维护友情,我们从始至终保持着某种默契,譬如我装作不知道安言喜欢她,她假装不知道我喜欢安然,我们彼此并不戳穿。
她与我和安言不同,她就住在那幢灰色的小楼里。第一次提出要去灰色小楼探险的是安言,安言让灰色小楼土著薛雀当内应的,可当我看到薛雀满脸通红,满含兴奋地打开楼门的刹那起,就明白了这个计划其实是薛雀想出来的。
薛雀是个洋娃娃般的可爱女孩,可爱的女孩需要更加多的呵护,所以我让她和安言走在一起。屋顶有盏总是闪个不停的日光灯。安言认为这地方有点邪门,因为听说换了很多次灯管,但每次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出同样的毛病。我觉得这只是因为潮湿的缘故,他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天花板也会潮湿,我解释不了。
我们三个人站在灯管下边,仰望黑色的木质天花板,突然几滴散发着恶臭的液体从裂缝中滴到薛雀的脸上,她发出尖叫,惊动了整栋楼的人。
后来大人们清理了烟道,发现里边堆满了猫的尸体。他们推测猫儿们是为了避寒钻进了这里,结果窒息而死。我心中却执拗的有另一个解释:象有象墓,猫有猫坟。它们知道死期将至,为了保持尊严,躲进了这个黑暗的空间悄悄离去。
薛雀的名字里带个雀字,麻雀怕猫天经地义,可这件事发生后,她反而对这些毛茸茸的家伙多了几分亲切。她曾经告诉我们,如果她要死了,也会像猫那样躲到一个无人的地方悄悄离去。
既然他能设法找到我,自然也有办法寻到薛雀,可他没这么做,是不是因为只有我才能分担他的这种痛苦?
“够了。”我突然停下脚步,“我不想再和你一起犯傻了。你别兜圈子了,我知道你有办法找到薛雀,你只是太害怕她死了,才拖延到现在。”
“现在你就给我去找,如果她还活着,那你明天就能处理掉那具尸骨,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”
我目光透过寒冷的烟雾,注视着街道对面的一家酒店。真的很巧,薛雀就是在那里告诉我她要结婚的消息。
“要是你确定这么做会快乐,我会去的。”我心不在焉地回答,“你不觉得现在结婚太早了么?”
我忘记自己接下来说了什么,反正最后是找了个借口告辞。薛雀在背后叫住我,脸上露出近乎哀求的愧疚,我生怕她为了安言的事道歉,违心地挤出笑容承诺自己一定会去参加婚礼。
安言终于打完了电话。“有线索了,”他哑着嗓子要我跟紧,脚步飞快地带我穿过一个铁路涵洞,来到了与咫尺之遥的商业区风格迥然相异的地方:摇摇欲坠的木制房屋,颜色艳得发腻的霓虹灯,随便推开招牌下的一扇门,浓烈的烟雾和刺鼻的酒味能把初来者呛得咳嗽不已。
他在这片可疑区域的边缘找到了目的地,一个名叫三脚猫的酒吧。我们找了两把干净些的椅子坐下,要了两杯啤酒,安言尝试着抿了一口,然后悄悄地吐到了桌子下。
顺着老板嘴角撇过去的方向看去,吧台边上一件蓝白相间的运动服非常醒目。黑色的长发披散在后背。安言有些焦躁地咽了口唾沫,走过去拍了拍那女孩的肩膀,她转过身。黑色的双瞳在蓝色眼影的包围下闪闪发光。
“我就是薛雀,”女孩的热情骤然冷却,回身继续玩她的手机。我注意到安言的肩膀激烈地起伏了几下,他终于控制住了情绪,从怀里掏出钱包,摸出几张百元大钞放在女孩面前。女孩犹豫了片刻,腾出一只手飞快地把钱装进了口袋。
十院是第十人民医院的简称,市精神病院的婉称。恐怕是因为精神病院对病人的隐私保护,才让安言没有第一时间找到线索。
医院入口十分隐秘,我们绕着布满枯萎常青藤的墙壁转了一大圈,才找到医院的大门。
在护士翻阅记录的时候,我偷看了一眼安言,果然,他不安得犹如在等待法官的最终判决。
“是有这么个病人,在这里住过半年多。”护士边查边说,“不过她在三年前已经出院了。”
护士若有所悟地点点头:“她病愈后自己出的院,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你还是去派出所查查吧。”
我还想问几个问题,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在门口出现,看见我们后扭头就走。我找了个借口离开,走出大门后发现昨晚在酒吧的那个女孩正在匆匆离去。
“看得出你有麻烦,我也有麻烦,咱们为啥不互相帮助呢?”我笑了笑,掏出几张钞票,“回答我一个问题给你一张,可以吗?”
“她本来就是个疯子。”女孩撇嘴道,“神经正常的话,怎么会嫁给女儿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人?”
拿光了我手里的钱,她扭头便走。安言铁青着脸走出大门:“刚才你和她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”
“这钱花得有点冤。”我目送着女孩穿过马路,伸手拦了辆出租车绝尘而去,“但我至少弄清了一件事,她恨薛雀,也不爱自己的父亲。”
总有一些人,当他们活着的时候,你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,当他们死后,才能感到深深地失落,而这些人往往是你真正在意的,很讽刺,不是么?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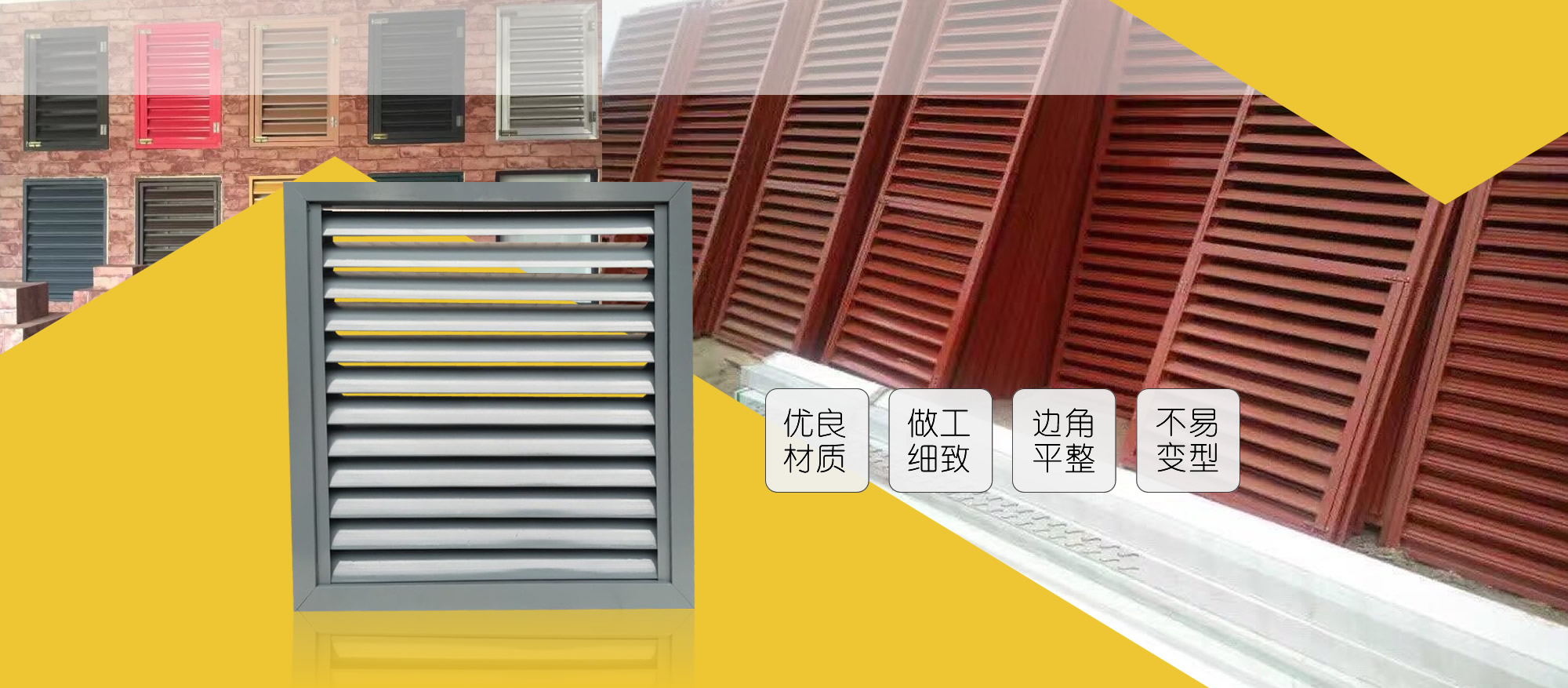
 河北省任丘城南工业区
河北省任丘城南工业区  张经理
张经理 19903172283
19903172283
 首页
首页 案例
案例 电话
电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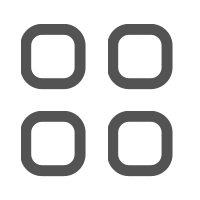 菜单
菜单